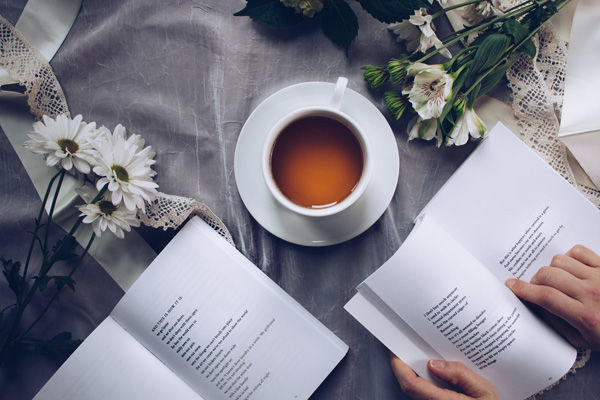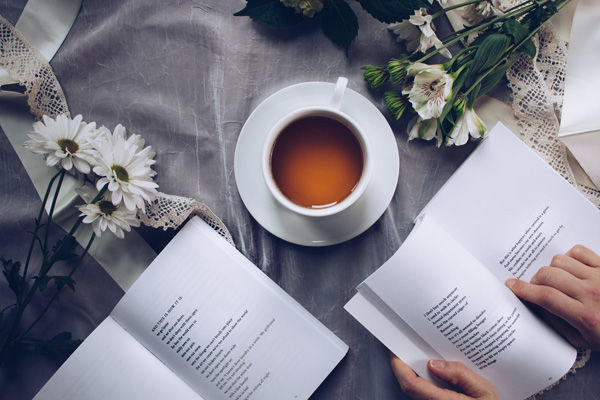【#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欢迎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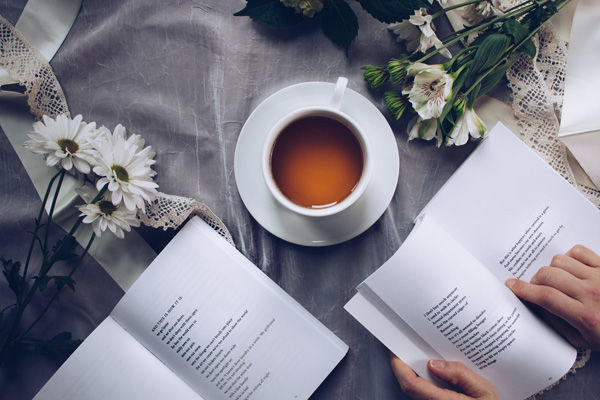
比“愧怍”更重要的是“害怕” 作者:黄邵震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2018年第46期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也就是说,只有以作品文字为出发点和载体才能真正领悟作者的思想情感。林筱芳在《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中认为杨绛的散文“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2]。换言之,杨绛的散文是将自己“绚烂华丽”的情感包裹在“沉定简洁”的文字之中的。对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它需要你有耐心肯动脑;当然这也是一种乐趣,它能带给你与作者精神深处的共鸣。 在《老王》一文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愧怍”即是惭愧之意,它出现在文末,本身又包含着明确情感指向,所以历来为论者重视。结合前文内容也不难看出,“幸运的人”当是杨绛自指,“不幸者”指的是老王。杨绛一家颇受老王照顾,她最后还拿了老王的香油鸡蛋,是一个“幸运的人”;而老王一生坎坷,遭遇各种不幸,直至最后孤病而亡,确实是一个“不幸者”。要说这样一个“幸运的”杨绛,因为占了“不幸者”老王不少好处却无法回报,因为自己拿出去的“钱”实在与老王付出来的“情”不对等,从而感到“愧怍”,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杨绛明明就在“愧怍”的前一句就否定了这种理解。她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是侮辱他?都不是。” 那么,杨绛到底在“愧怍”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回到文章,沿波讨源,披文入情了。其实,要理解杨绛的“愧怍”,首先要看到她的“害怕”。“害怕”是打开“愧怍”这扇门的钥匙,是杨绛真正的苦心经营之处,是杨绛深埋于平淡文字之下骇浪惊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比“愧怍”本身更重要。 在文章的第六节,杨绛首先特别清晰地点明了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接着叙述,因为钱钟书先生的腿出了问题,所以请老王用三轮车送钱先生去医院。随后,杨绛写了这么一句:“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这句话实在太让人惊诧了!“不敢”乘三轮?是怕自己年纪大了不适,怕老王驾驶技术不好,怕车子安全系数不高,抑或是怕路上坑洼颠簸不平?显然都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忘记,本文的第一句话,杨绛是这么写的:“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一个“常坐”三轮,且能“说着闲话”的人,当然是一点也不会怕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 那么,杨绛在害怕什么?也许从她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一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文革开始后,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牛鬼蛇神”中的一种,他们的境遇极其糟糕。在《丙》一文中,杨绛写道:“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3]除了挨骂挨打挨整挨斗,“牛鬼蛇神”们在身体上也被留下明显的标志。杨绛写道:“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4]有了这样明显的标志,哪怕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会遭到各种攻击。杨绛记录了一次她乘公交车的经历:“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5]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362652d74a20029bd64783e0912a21615797fb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