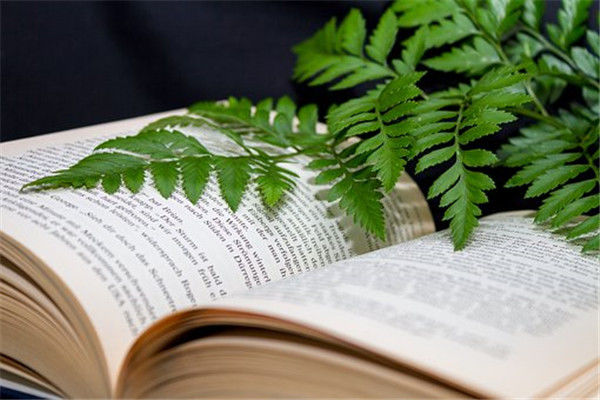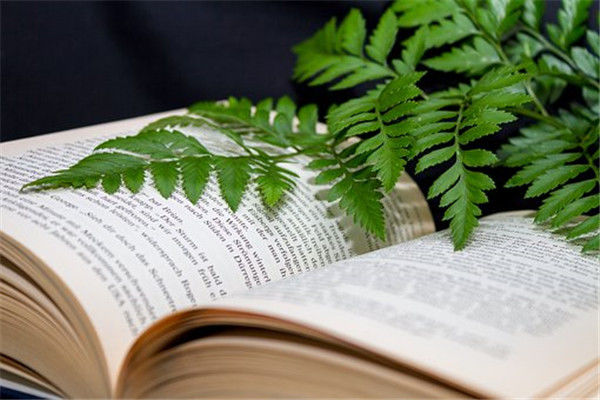【#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西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理论思想的演进》,欢迎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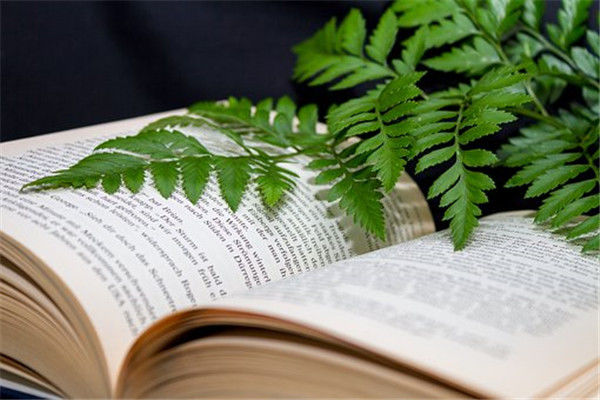
第二章 西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理论思想的演进 社会建设和治理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体现。从古至今,人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思想和模式。就西方而言,其主要源于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并经过复杂漫长的融合、创新和演变之后,于近现代逐渐成熟起来。总起来讲,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法治下的民主社会,它的管理自然也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其特点是把人权或公民权利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社会建设和管理被认为是一种把传统的人转变为现代人的“规训”过程和“文明进程”。 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非总体性的分化和分工相当精细的社会,因此,严格地讲,它们并没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综合性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这样的词汇,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认真考察的话,也能够在西方人管理实践和理论中挖掘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某些制度和思想。只不过由于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其理念、方法和实践往往大不相同。 一、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取向: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自由是西方的“最高政治目的”(赫尔德,2004:327)。作为“一种文明的造物”,它把人从具有反复无常要求的小群体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然而,如哈耶克所言。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经由那种同时也是自由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freedom)的文明之规训(the discipline of civilization)的进化”造就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哈耶克,2000:512)。因此,社会秩序,“作为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卢梭,1982:8),与自由同样具有最高的价值。两者既有张力,又相辅相成,并在法治下“开放且抽象的社会”趋于适当平衡。这既是现代西方社会本身持续稳定的内在原因,也是其社会建设和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西方,自由与秩序关系问题由来已久。远在古希腊,通过修昔底德(Thucydides,1972:145-149)、柏拉图(2002:第八卷)、亚里士多德(1981:卷六)等人的著作,我们知道,“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公民)曾经享有较高的“自由”。① 他们可以直接选举城邦的领导和“法官”,民主制定法律,共同参与城邦管理。类似地,共和时期的古罗马人(公民)通过“宪政”(西塞罗,2002)也反映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尽管罗马人在公法上的法治建设远非私法那么出色)。因此,“自由”早在古典世界就已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取向。这是一种虽不安定但却充满活力的因素,对后世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产生深远影响。不过,按照贡斯当(2003:45-68)的说法,希腊-罗马的这种自由只是“古代人的自由”,而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主要表现为公民“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因此,这种自由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自由”,其类似于后来托克维尔(1992)、韦伯(2005a)等人所说的共同体式的“自由”,或斯金纳(2003)所言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换言之,它只是政治自由,不是“个人自由”。古代人不仅没有现代西方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人权或个人独立性,而且所有私人行动和领域“都受到严格的监视”,甚至干预。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贡斯当,2003:48)。 ①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通常说每一平民政体莫不以自由为其宗旨”(1981:卷六1317a-40-1318a-10)。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公民权利)只限于有雅典城邦公民身份的成年男子,而妇女和儿童、外来没有雅典身份的自由民、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是没有这种自由权利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古典世界,一方面是“集体性自由”,另一方面是个人为共同体所吞没。不过,如贡斯当所言,当时人们觉得承认个体对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与这种自由之间没有什么不容之处。大概除了柏拉图等极少数人外,雅典人并不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现存管理范式和秩序本身出现问题。这表明,即使在开明的城邦,自由不能超越“集体性自由”的范围,它必然受到特定的宗教秩序以及受此影响的熟人社会习俗的约束(苏格拉底反荷马向度的文化必受惩罚)。尽管在希腊古典时期“以哲学发展为秩序的符号”开始兴起(Voegelin,2000),但传统宗教秩序仍在发挥强大的作用。这种秩序作用就在于它们给现世或人们带来确定性和意义,也就是持续的普遍安全感以及内心和社会的有序性。涂尔干(1999:550)说:“宗教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生活下去”。弗洛伊德认为,若没有宗教信仰和种种禁忌,人类可能早就绝灭了。因为这种与人类社会结成一体的宗教秩序给人以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驯制人的炽情,把非理性力量引入对共同体或社会有益的渠道,最终使世界成为人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差强人意的世界(Freud,1957:54)。在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认为(2002:562-564)过分自由和极端民主会把人类引向崩溃,“极端的自由……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是十分有道理的。 因此,自由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与之相应的秩序的“规训”。与自由同样,秩序也是古典世界的最重要的文化取向。两者在古典世界构成彼此相关,但又相互矛盾并形成张力的向度。对于雅典城邦或共和时期的罗马而言,这两者都是弥足珍贵的价值。管理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取得这两者的基本均衡或和谐。而“和谐”按赫拉克利特的解释则“是对立物间张力的结果”(伊利亚德,2004:233)。实际上,古典世界一些著名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都对雅典伯利克里时代平民大众民主自由评价不高,因为他们依据经验和理论懂得在缺少理性法治的情况下这种平民自由往往演变为“集体君主”专制(亚里士多德,1981:卷三、卷四),即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在管理上寻求均衡与和谐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思想。 对于西方而言,没有自由的秩序是可怕的,但无序的自由同样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有时,这成为困境,因为真正的和谐或均衡毕竟难求。希腊古典时期末期,随着“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语)观念的兴起和荷马向度的传统宗教文化的逐渐式微,滥觞于苏格拉底的人文哲学符号秩序出现了。不过,这种秩序似乎既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也无法拯救失序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宗教四起,最终犹太-基督教脱颖而出,并在此后更加动乱的年代登上历史舞台。这表明:一方面,古典世界后期社会自由度在增加;另一方面,希腊罗马社会-文化向度(不论神话宗教向度抑或人文哲学向度)的秩序无法解决这种自由带来的问题。换言之,这种秩序本身无法解决希腊-罗马文明崩溃的问题。因为受种种条件限制人尚未进化到大致知晓如何较好规训自由的地步。于是,物极必反,秩序的建构便走向另一个方面,即救赎或启示宗教共同体方面。基督教起初作为一场微不足道的自发性弥赛亚运动,之所以能够最终占领西方舞台,除了韦伯所分析的“超越性”、“救赎与再生”(“福音”)等因素外(韦伯,2005b),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价值重估”,它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使本就是社会动物的人在内心和世道都已混乱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安定和有序。 因此,基督教给失序的古典世界带来了新的向往和秩序。它虽然没能最终保住“世俗之城”的罗马,但却通过“天城”使人们在精神上重新变得文明有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奥古斯丁,2006:下卷)。“天城”的延续和兴盛为西方中世纪社会秩序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基督教为核心重建西方的秩序便不可避免。从社会建设和管理上看,这也符合西方历史发展的要求。因为当时西方世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桀骜不驯的“蛮族”,实现教化或文明化。而基督教化在当时则是这种教化或文明化的无二选择。它成为抵制野蛮和倒退的主要堡垒(曼海姆,2002),有助于人们向善和规训“封建自由”(拉吉罗,2011),推动教育、学术研究、医疗、赈灾、慈善等事业发展,为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和国家的建构,提供了最早的样板(伯尔曼,1993: 246、139)。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复杂艰苦斗争实现的。公元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发动争取“教会自由”的改革(“教皇革命”)(伯尔曼,1993:111),随着“两剑论”① 付诸实行,西方在一种矛盾着的状态下,基本上被统一在一个“基督教母体”内来管理。基督教成为凝聚西方的黏合剂,并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秩序和意义。这样,我们看到,在中世纪盛期,教会在获得某种“自由”之后逐渐演化为一种精神和权力秩序。 不过,随着教会享有权力和利益的增多,这种秩序也越发固化和僵化,于是,悄然兴起的世俗自由因素不断与之发生冲突。它们先是表现为所谓的“封建自由”,以后作为“特(许)权”(libertise)更多地体现在自由市、行会、乡村公社的相对自治之中。法国作家兼评论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年)说“在法国,自由是古典的,专制才是现代的”(拉吉罗,2011:1),指的就是这些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在中世纪比在后来的绝对主义时代似乎更多一些。当然,直到宗教改革以前,这种自由大体是在一只无形的手,即“耶稣基督之手”(迈克尔•曼语)的“规范调节”下开展的,并与基督教社会秩序趋于某种平衡状态(阿奎那的主要著作反映了这一特点)。 西方近现代对自由与秩序问题的明显关注导源于中世纪盛期教廷(教会)与世俗权力之争。这种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上的二元结构不仅导致“文化领导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而且给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并最终成为近现代西方产生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自由的“主要因素之一”(Dawson,1958:chapter one)。它把西方社会从自由因素的成长逐渐引向法治下保护和规训自由的现代性秩序建构。西方学者经常把西方的这段历史进程与穆斯林社会情况进行比较。他们认为,当时,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突出区别在于,西方的二元管理模式能够给予世俗管理以更大的相对独立性。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世界,由于以神启戒律或无所不包的社会命令严格规定人们所有的公私生活,并且一开始便排出了理性可以从中独立发挥作用的活动余地,因此本来已有所发展的哲学、科学和民间自主性最终被窒息在摇篮里。而基督教社会由于通过两种不同的权力和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来管理,广大信徒才有可能在许多方面按照并非基督教特有的原则或标准来相对自由地组织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2009:235)。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再加上其它因素,西方文化和社会中的自由因素才获得不断增长。这种自由经过曲折复杂的过程,从路德所说的“基督徒的自由”(路德,2004)转变为世俗公民自由,从中世纪的特许权逐渐发展成为普遍权利,从共同体的自由延伸到个人自由,从上层阶级的人权逐渐向中下阶级扩展,基督教母体的秩序和封建秩序终于遭到分解。尽管人们对自由存在不同理解,但“现代人的自由”毕竟产生了。用康德的话说(Beck,1959:85),人终于长大成熟,从“自己加给自己的监护状态下解放出来”,从此自主行事而不再需要教会或国家告诉他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了。 随着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社会自由度的急剧增加,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的上升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共同体”也日益向滕尼斯所说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转变(滕尼斯,2006:39),与此同时,人也由共同体的人转变为“原子化”的“社会人”。这是一个人与社会剧变的时代。然而,如同其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遭到惩罚一样,现代人的自由和解放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突出表现为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失范”和失序。这是西方形而上学、上帝和乌托邦先后遭到解构的结果,也是“神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2001:124)又一次转向“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必然结果。由于古典世界晚期曾存在类似现象,因此索罗金认为这是西方的一种轮回(Sorokin,1937)。当然,人类发展的法则总是具有两面性:一面是解放,另一面是强制。在现代西方,自由与秩序总是通过复杂的互动相伴相随,也就是说,自由只有经由“自由之规训”才有可能。因此,正如鲍曼(2007:29)所言,19世纪 ① “两剑”指“精神之剑”(spiritual sword)与“世俗之剑”(secular sword)。“两剑论”意指在保证教廷至高无上地位的条件下,精神世界由教会管理,世俗社会归皇(王)权统治(参见Tierney,1988)。 不仅是“伟大的错位、解脱、脱域(disembeddedness)和根除(uprooting)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不顾一切地试图重新承负、重新嵌入、重新植根的伟大世纪”。西方在英国和法国革命后,随着自由的成长,建构相应的新秩序便成为不能不完成的主题。与以往相比,这个主题的实现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也就是如后来社会学家所说的,它是一个“现代性工程”(Giddens,1994)或“社会工程”(Bauman,1991)。 不过,治理失范和失序,建构维续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秩序,主要采取何种方法,亦即主要靠法治,靠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协调互动,还是主要依赖强权的严厉行政手段,当时人们并无定论。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尽管推崇“现代人的自由”,但也对“自由放任”存有必要的戒心。作为早期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2008)就指出注重道义和遵从社会准则的必要性。他主张要合乎道义地“利己”(在利他中利己),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和谐(Morrow,1963)。同样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1995、2000),更是与众不同地要求政府通过严厉监管来建构和维护现代社会的秩序(尽管他是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的)。边沁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意味着总会有某些人的幸福不会而且实际上也不应当得到满足。因此,对于那些威胁公共福祉的不服从者(不论个人、集团还是阶级)必须实行严厉管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上述原则的实现。边沁以大多数人福祉的名义提倡建构一种新型权力系统,对社会中的人们进行管束、调教和型塑,也就是后来福柯(1999a;1999b)所指称的“规训”。这种“规训”,按福柯的解释,以分布在整个社会结构并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为核心,通过公共秩序、监狱、规范、法律、教会、诊所、学校教育、宗教忏悔、文化知识等等,塑造特定的符合近现代性要求的个体、制度和文化安排。也就是说,近现代历史被视为一种通过或明或暗的约束和规范技术而产生现代自我与社会的过程。这也是政府控制与“自我的技术”的巧妙结合(福柯,1998;Foucault,1984)。由此社会建设和管理被隐喻为边沁发明的一种“全景监狱”(Panopticon,环形监狱)系统的延伸。从这一点出发,为了型塑现代人与社会,或者每当“自由放任”或市民社会不足以确保他们所说的最佳可能的结果的时候,国家就有理由进行干预和规范,以此来重建社会关系、秩序和个体。其实,自由主义在重视个人主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不要社会监管。相反,如约翰•密尔所言,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行动上都“必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人们不仅不应当彼此损害利益,而且有责任和义务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遭损害而付出自己一份劳动和牺牲。“若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密尔,1982:81)。因此,自由主义是主张监管的,只不过强调这种监管要恰到好处(搞清楚需要监管多少),反映公益,不可“独断专行”(洛克,1981)。 一般而言,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主要表现为强制权力的监管——Z•鲍曼(2007)称为“全景监狱式”监管。不过,此后随着社会学的发展,对人的研究逐渐由“经济人时代”过渡到“社会人时代”,以及梅奥主义的出现对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上越发向着更人性化方向转变。这种“全景监狱式”监管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维续上越来越不适宜了。 那么,在现代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究竟如何进行?西方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自然离不开其一贯强调的平衡原则。围绕这一点,其主要涉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二是如何对待法治与行政干预以及怎样保护合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三是如何建构一种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最终从双方都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的社会秩序。 关于第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S.M.•利普赛特(1993)就指出,现代社会和政治系统如果要获得稳定有序运行的话,不仅需要外部经济发展,而且更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取得“冲突与一致的适当平衡”。因为只有在这种平衡中才真正有助于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那么在两者之间如何建立平衡呢?这就是法治下“社会意义上的民主”(托克维尔,2004;阿隆,2009:12)。在此,关键之处是国家能否成为不再专受某一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控制的“仲裁者”。它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上以法治和国家理性为基础真正做到公正合理、不偏不倚,能够合理平衡现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说以往,比如二战以前,这一点难以实现,那么在战后便有了现实可行性。战后随着中等阶层的崛起和在社会中占据多数,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2001;Bell,1988)(确切地讲,应当是解构而非“终结”),某种意义上国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某些特殊人群的代言者而是在不断的治理中越发接近成为“仲裁者”。因此,以往那种主要依靠权力所获得的一致性日趋降低,而协商、合作和服务机制则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冲突仍然存在,但大都被纳入法治的轨道和得到有效的“规训”:冲突受到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和机制的抑制,并通过它们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也就是说,如雷蒙•阿隆所言,法治下的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并非是为了平息冲突,而是为了避免让它们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达仁道夫,2000:141)。这也就是管理冲突并使之法治化、理性化和非暴力化。因此,在自由民主社会,冲突不仅不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社会的改良。正如阿隆在阐述托克维尔观点时所言的那样,一个中产阶级占优势的社会“因不断的要求和利益冲突产生动荡,但不太可能发生革命”。 关于第二个问题,较早时候,W.李普曼曾经说过:“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国家并不通过行政的手段管理人们的事务,而只是通过法律调整人们的私性活动”(Lippmann,1973:267)。李普曼这一正统自由主义的说法,尽管有些理想化(因为即使在现代西方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行政干预),但却反映了现代西方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上的一贯思想和向往的境界。多少年来,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也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它们的主要做法一是坚持实行法治(而不是法制),不管政府还是社会的活动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而法治是相对独立的)。其实质是究竟想要自由民主的制度,还是想要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做法。其次,国家立法保护合理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因为它们是社会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一般而言,大凡缺乏自发性和自组织性合理存在和成长的社会,其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也较低。因为发明创造不是权力机构人为设计和安排的结果,而首先是一种自发和自组织的过程,然后才是自觉选择和有系统有理论的提升过程。第三,强调国家干预的扩大不等于行政干预的扩大,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导致当代西方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上尽可能地减少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高压强制,更多地采取一种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在法治范围内有序互动、协调和合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如鲍曼所言(2006:13),管理更多地体现为服务(国家活动的扩大主要体现在这方面而不是传统权力支配方面),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法治的市场模式,公共关系取代了“命令”,吸引和诱惑更多地被放在过去严厉刚性制度占据的位置上。简言之,传统的权力整合技术总体上不再作为对待社会主流(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上等阶层)的控制手段,而主要用于对少数“下等阶层”的“失范者”和失序者(懒惰、吸毒、流浪、或无家可归者等等)的管理。当然,整体上国家仍保持很大的强制力,但它必须受到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制约。显然,这是哈耶克所言的那种现代西方“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以自由与抽象规则和秩序的平衡为基础的,因而是一种法治下开放且自由的“抽象社会”的管理模式。在现代西方,这种“开放且抽象的社会已不再是经由追求共同且具体的目的而只是通过服从同样的抽象的规则而凝聚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抽象社会的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理解,而且人们为了维续此种秩序而不得不服从的那些规则“也往往是与人的先天性本能相反对的”(哈耶克,2000:513),因为西方法治下抽象社会的运行所基于的更多是情感中立、自我取向(利益优先)、普遍主义和自致性而较少是情感、集体取向、特殊主义(我群主义)和先赋性(Parsons & Shils,1951:77)。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主要基于法治条件下的抽象或一般性社会关系、观念,依赖于有很高可信度和确定性的一般规则和程序,即主要依赖于理性化的公民责任、公民义务,而不是不稳定的行政干预以及往往与此相关的在背后起作用的个人纽带、个人忠诚、个人情感,以及乡党、朋友和伙伴小群体关系。现代西方社会运行何以较为稳定,其内在秘密就在于此。 第三个问题涉及自由文化本质问题。现代西方抽象社会自产生之日起,便不断遭到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攻击,其主要是指责这种社会无视人们的民族和文化特色,脱离与各种价值观、信仰和传统的联系,压抑直觉和灵性的东西(不懂得非理性还有正面积极意义)。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生活在熟人社会(传统共同体),就可得到传统的那一套东西;而要生活在现代性陌生人社会,就只能靠抽象的规则形成秩序。这或许是西方自由文化演化的宿命。因为最终只有在抽象的社会(在抽象的秩序中),个人自由才能真正生存和伸展开来,人才能摆脱“臣民”状态而获得一般意义的现代公民权利和“尊严”。因此,希望平等享受现代自由和获得尊严的人们别无选择。此外,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社会或许不怎么喜欢传统的约束,不反对把它们废除掉,但它却致力于提出新的自身‘新改进的’约束,一点也不容忍个体亵渎这些规范”(鲍曼,2006:5)。这就是说,在开放且自由的社会,自由是要受到规训的,但由于人们所享有的唯一共同的价值不再是某种有待实现的具体目的,如某种保守或激进的设想、或乌托邦计划,而只是那些能够确使一个抽象秩序得以持久维续的共同抽象行为规则,因此,这种作为规训的规则和秩序只保证向个人提供他得以实现其个人目的的较好条件、较好环境和前景,而“不赋予个人以要求特定东西的权利”(哈耶克,2000:513)。在此,我们看到,只有在这样一种开放而抽象的社会中自由与秩序才可趋于一种差强人意的新的平衡。进一步讲,只有抽象的规则才能避免因强制推行某种具体共同目标而导致的冲突,才能满足各种多元的、追求不同目的的自由人们的需要,从而把他们整合在一个和平的秩序之中。总之,只有在这种开放且自由的“大社会”,才有可能把卢梭所说的那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处于不断相互猜疑、彼此防范,以及双方都不自由的奴隶状①态下解放出来。 这是当代西方社会本身内在稳定之所在,也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取向和向往的境界。② 二、社会控制理论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典型的社会学观念:“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智识脉络,并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社会学的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传统,构成了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虽然首先在美国早期社会学中予以阐发,但鉴于它与社会学的一些核心论题——尤其是社会秩序问题、失范与越轨问题——的密切关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勾连社会学诸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 “社会控制”这个术语最初“作为社会学考察社会秩序问题的一个综合性的基础……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依据所期望的原则和价值来调节自身的能力”(Janowitz, 1975: 82)。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组织和管理自身的能力。早期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强调对价值承诺的依赖,因此与“强制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有截然区分,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后者视为它的对立面。社会控制意在减少强制和消除人类苦难,强调用理性与科学的手段及程序实现社会的目标或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具有美国早期社会学鲜明的“社会神义论”(sociodicy)色彩(Vidich & Lyman, 1985)。另外,从“社会控制”的 ① 卢梭言(1982:8):“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是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演进的。 ② 当代社会理论和经验证明,在真正法治下的民主社会,由于其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确定性,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点。因为作为规则,这是目前人类所能想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最佳规则。 早期应用来看,它也不能等同于稳定、遵从(conformity)及压制,相反,它要“将分裂、张力和紧张组织起来”;问题在于:“社会控制过程是否能够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依然能够进行转变和社会变迁”(Janowitz, 1975: 85)。社会控制在心理和人格层次上的对应物是“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后者的关注点是“一个人在把对其本人和其他人的扰乱与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同时引导其能量和满足其需要的能力”(Janowitz, 1975:84)美国早期社会学对于教育、社会化及自我等问题的探讨,某种意义上针对的即是社会控制与个人控制的关系问题。 “社会控制”观念的提出与美国社会学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社会及智识背景密切相关。在美国“内战”之后出现的“镀金时代”,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移民潮等导致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整个社会虽充满活力但也动荡不安,新旧交替使得社会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紧迫的问题;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其时代问题的或被动或主动的回应。作为所谓的“第一个新国家”(Lipset, 1979)的美国,自殖民地时代起即深受新教的影响,1870、80年代兴起的“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即体现了新教对其时代问题的回应,美国早期社会学也深深打上了“社会福音”的烙印,许多社会(科)学家试图借用美国自身深厚的宗教资源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社会控制”观念最初的提出实质上即为社会重建的一种对策,并籍此引领美国社会实现其世俗道德理想(譬如建立“上帝在尘世的王国”)。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则在更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及智识的层面上对社会控制观念的提出和扩散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当然,最具美国思想特色的“实用主义”因为强调行动主义、教育与控制以及道德理想,从而为社会控制观念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智识基础。这些具有内在关联的因素(当然不止于此)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式的现代性,而社会控制的观念即为其表达形式之一。正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早期成员文森特所言:“社会控制是将各种社会力(social forces)结合起来的艺术,以便为社会提供一种迈向理想的趋势”(Vincent, 1896: 490)。 分别深受斯宾塞和孔德影响的美国早期社会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萨姆纳(W.G.Sumner)和沃德(L.F.Ward)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实际上体现了自由放任与社会干预(控制)之间的对立。“社会控制”主要承续的是后一种进路。而美国1930年代的“新政”进一步彰显了美国社会思想的这种主流趋势。所以我们在帕森斯(T. Parsons)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的开篇看到的是一个颇具深意的宣告:“斯宾塞(式理论)已经死亡”。或者更准确地说,斯宾塞所代表的那种“曾在英语民族的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理论传统”(Parsons, 1968: 3)已经式微。帕森斯的这种宣告基于他的这样一种智识发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思想传统内部发生了一场堪与17世纪的思想革命相媲美的思想运动(Parsons, 1968:5),涂尔干、韦伯和帕累托等古典社会理论家即为这场思想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接续涂尔干、韦伯等前辈对曾经主导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展开系统的批判,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功利主义的社会理论体系”的批判中(Parsons, 1968: 51-60),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不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他们开辟的功利主义理论体系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秩序问题”,换言之,功利主义的“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和自发调节机制或“自生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是很不充分的,在自由与决定论这一核心问题上最终会陷入“功利主义困境”(utilitarian dilemma)。而涂尔干、韦伯等人的理论则趋向于他所谓的“意志论的行动理论”(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这种理论取向既强调行动的“规范性取向”,也重视行动者面对各种客观的“情境因素”,同时强调“努力”实现目的或理想的“意志论”取向,因此能够更有效和充分地处理“行动和秩序”问题。帕森斯早期虽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早期社会学传统,但在“集体无意识”的意义上接续了整个传统。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控制”的观念针对的正是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 虽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1892)中使用了“控制”(control)这个词,但它在斯宾塞的理论取向中显然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罗斯(E. A. Ross)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探查秩序的基础》,是社会学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社会控制”问题的论著。从该书的副标题即可看出,其探讨的主题显然是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罗斯认为,基于同情、友善和正义感的“自然秩序”是“粗糙和不完善”的,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秩序而言,社会控制是必要的:“如果不打算让我们的社会秩序象纸牌搭成的房屋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它们。自由放任的政策——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同时也是教育、公共舆论、宗教和暗示方面的——无疑会有助于十七世纪北欧流行的那种混乱在我们中间复活”(罗斯,1989: 43)基于此,罗斯对“社会控制的手段”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其中既包括“舆论、暗示、个人理想、社会宗教、艺术和社会评价”之类“从原始的道德情感中吸取大部分力量”的控制工具(他称之为“伦理的”),也包括“法律、信仰、礼仪、教育和幻想”等“全然不需来自道德情感”的控制手段(他称之为“政治的”)(罗斯,1989:313)。罗斯虽然承认法律等制度性控制的重要性,但基于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更为根本、也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必定是富有情感的并触及人们的内在精神领域,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于“社会宗教”(social religion)的论述中。罗斯认为,人类古老的家庭单位中产生了两种情感:(对家长的)“孝敬”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同情”,前者是“服从和义务的根源”,后者是“伙伴关系和手足之情的根源”。这两种情感渐渐地发展出两种宗教类型:“法定或律法宗教”(legalistic religion)和“社会宗教”(罗斯,1989:154)。“社会宗教”所强调的博爱或兄弟情谊(fraternity, brotherhood)虽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罗斯更多地强调的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一种彼此接近的纯洁的宗教感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能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毋容置疑,在精神上联系起来的人们的信念,在修正人们的行为中是最有效验的”(罗斯,1989:160)。作为社会学家,罗斯“在根本上所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创造出(现代社会中的)和谐关系的社会条件”(Janowitz, 1975: 89)。 罗斯同时代或稍后的一些社会学家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了对“社会控制”的研究。例如托马斯(W. I. Thomas)、库利(Ch. H. Cooley)和米德(G. H. Mead)等人开辟的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传统,从“社会化”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个人的“自我”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社会”(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参与到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社会化过程不仅仅是个体“内化”社会价值观和规范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自主性(自我、人格)的形成过程。这种研究传统虽然侧重个体互动的所谓“微观社会过程”的研究,但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框架基本上都在微观-宏观层次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例如托马斯关于(个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的研究,库利关于“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初级群体”以及社会制度的分析,米德关于“主我”(I)—“宾我”(me)以及“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分析。因此,自我、人格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控制”(self-control)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控制”过程,或者说,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维度。 另一方面,“社会控制”的观念在美国早期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化,这尤其体现在“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研究中。帕克(Robert E. Park)和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领导和指导了该学派在1920、30年代的经验研究,他们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教科书《社会学导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是社会控制问题”(Park,1967: 209)。帕克将社会学界定为研究“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科学”,社会不止于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个体,“因为存在着(1)某种社会过程和(2)这种过程所产生的一些传统与舆论——它们具有某种相对客观的特性并作为一种控制的形式,即社会控制而施加于个体身上”,因此,社会控制成为“社会的核心事实和中心问题”(Turner, 1967: x-xi)。帕克认为:“社会无处不是一个控制组织。它的功能就是组织、整合以及指导作为社会的构成成分的个体身上所蕴含的能量。也许可以这样说,社会的功能无处不是限制竞争,并通过这种限制而实现构成社会的诸有机单位间的某种更为有效的合作(Turner, 1967:83)。”因此,社会控制与集体行为适用于相同的对象,所不同的是,社会控制指涉的是“机制”,而集体行为指涉的是“过程”(Turner, 1967: xii)。帕克对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尤其是舆论和制度等控制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另外,帕克基于他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自然史”研究而对社会过程作出了明确的阶段划分:由竞争、冲突到调适(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再加上他对“生态秩序”(ecological order)和“社会秩序”的生态学研究,拓展和深化了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这一核心论题。 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现代城市(尤其是芝加哥这个“巨大的天然实验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领域,诸如“游民”(hobo)、“黑帮”(bang)、“聚居区”(ghetto)、“贫民窟”(slum)、“自杀”、“家庭解体”、“旅馆生活”、“职业舞女伴舞舞厅”(taxi-dance hall)、“青少年犯罪”、“有组织犯罪”、“白领犯罪”以及移民、种族关系这些美国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Bulmer, 1984;Faris, 1970)。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大都可以视为在托马斯、帕克等人的相关理论框架的影响和指导下的对于“社会控制”观念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使社会控制观念具体化和深化,同时,尤其是其中大量关于越轨与犯罪的研究也使得早期“社会控制”观念那较为宽泛的意涵出现“狭义化”的倾向。除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外,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其他研究领域,如制度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也都借鉴了“社会控制”的观念,涌现出大量的相关研究。 帕森斯在其“第一次主要综合”(Parsons,1968)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帕森斯式”(Parsonsian)理论,这种理论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帕森斯的社会理论解读为一种社会控制论。帕森斯早期对“霍布斯秩序问题”的独特论述以及相应地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和他对涂尔干、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的解读,都可以看出他深刻意识到“社会控制”观念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虽然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术语。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过渡期”,帕森斯撰写了大量“经验论文”,其中有些明确论及“社会控制”的问题,如1942年发表的长文“宣传与社会控制”(Parsons, 1954/1942)和讨论战后德国问题的“控制性制度变迁问题”(Parsons, 1954/1945),不过,他是在狭义上来使用“社会控制”概念的。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辟专章讨论“越轨行为与社会控制机制”(Parsons, 1951: VII),并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控制”的四种“机制”(Parsons, 1951:298)。① 实际上,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同时表达了广义和狭义上的“社会控制”观念:他论及的“社会控制机制”基本上是就其狭义而言的(这也是“二战”后对“社会控制”的通常用法,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学教科书都会专辟“越轨与社会控制”章节),但他这个时期重点阐述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图式以及他用“内化”(internal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概念来联结人格、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以明确的分析概念表达了广义的“社会控制”观念,或者准确的说,是将“社②会控制”的广义和狭义两种意涵联结起来了。 随着帕森斯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复杂化,尤其是“控制论意义上的等级”(cybernetic hierarchy)和“一般化的符号交换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a of interchange)的引入,其系统理论也日益表现为一种“系统控制论”。不过,透过这种形式化的理论外壳,我们依然能够看出帕森斯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都对社会控制理论做出了巨大的推进。 从现代社会学对“社会控制”概念的使用来看,基本上是就其狭义而言的。换言之,随 即“支持”(support)、“许可”(permissiveness)、“对互惠的否拒”(denial of reciprocity)和“对报偿的操控”(manipulation of rewards)。 ② 帕森斯的这种研究进路与社会学中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与“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的区分(洛克伍德,1997)密切相关。实际上,洛克伍德正是在对帕森斯的批评基础上提出这对概念的。 ①着社会学研究的“去道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社会控制”观念也越来越收缩为一个理论和经验研究中的分析性概念。这尤其体现在越轨、犯罪等研究领域里关于“社会控制”的大量“中程”(默顿意义上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在关于“社会控制”的社会系统论的研究进路中,卢曼(N. Luhmann)无疑是帕森斯理论的最重要的推进者,当然,其中的抽象性、程序性和技术性的色彩也更加浓厚。帕森斯之后对社会控制理论之发展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福柯(M. Foucault),不论他对于“权力”的突破性分析,还是他晚期更加注重的对于“主体”问题的研究,都极大地推进和拓展了“社会控制”理论,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限于篇幅,不再就此展开。 三、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社会建设和管理 “宪法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西方的自由(人权或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三大支柱”(达仁道夫,2000:36)。这三者的存在状态和互动情形如何,直接关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和秩序的维续问题。进一步说,在当代西方,随着制衡机制的发展,社会建设和管理愈来愈不再是国家(居高临下地)在“型塑”意义上管理社会的问题,而是以上三者,尤其是国家与社会,通过法治进行有序互动的问题。其中,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基础,而法治国家则变成其“保护神”。因此,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不仅涉及前两个方面,而且还包括国家(政府)的治理。使国家如何向善和保持正义及理性,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它牵扯到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神经。 远在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1981:卷一)就说过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或“趋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作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城邦以正义为原则”,而“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是想告诉人们人类与其他群居性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在行动中寻求“正义”。然而,正义问题不是个人本身能够解决的,它与城邦相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正义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正是对正义的寻求(“求取善果”),人们才在政治上组合成共同体(Politike Koinonia)。这一思想后来成为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范式,对包括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在内的近代社会理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从实然的角度讲,作为国家的城邦并非天然正义和向善,因为它是“建构的”(made)(哈耶克,2000:475)。人造的国家是否维续正义和善治,其本身不能确定,而取决于管理的形式。因此,早在古希腊就有雅典与斯巴达两种模式之争。前者凸出自由民主主义,后者则主张总体性的国家主义或“斯巴达式共产主义”(恩格斯语)。柏拉图欣赏斯巴达模式并把之升华和理想化——其“理想国”就出自“斯巴达幻象”(the Sparta mirage),而亚里士多德则看重“混合政体”(他是这一概念的创始人)(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2009:132),意指“一种改进的贵族制”(贵族共和制),或“改进的民主制”(梭伦式有限民主,区别于伯利克里式大众民主)(莫斯卡,2002:505)。亚里士多德比其老师看问题要现实得多。他没有从应然出发迷恋于无法达到的“绝对至善”的管理模式(理想国或乌托邦),而是从实然出发研究尽管不怎么完善但却现实可行的较好管理模式。通过广泛比较,他认为最好的现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就是混合体制,因为它兼顾了不同体制的优点。此后,波利比阿(Polybius,2007)、西塞罗(2002)、阿奎那(Aquinas,1964)都对混合体制抱有好感。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良好的管理不仅要体现正义,而且还要有理性。而保持国家理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由中产阶级执掌国家权力进行管理。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的“中庸”地位决定了他们比富豪与穷人都更加趋于理性,能够克服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把派别冲突降低到最低程度,因而能够维续国家理性,使政体乃至社会更加趋于稳定和持久(亚里士多德,1981:卷四)。当然,由于中等阶层在古代社会人口中只占少数,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当时难以引人关注。古希腊这两种管理模式和不同思想家的理论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取向,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张力,多少年来成为西方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两种不同传统和不尽文化源泉。只不过,在西方,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前者成为显性的主流,而后者只是时隐时现的支流。 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的混乱往往与国家治理的好坏相关,因此社会建设和管理首先被认为是一种如何维续国家善治和正义的问题。以往苏格拉底、柏拉图或基督教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地置于“美德”或信仰之上,因而寄托于某种理想或乌托邦世界。与此不同,从“现代政治哲学奠基者”(列奥•施特劳斯语)马基雅维利(2005)开始,思想家们便把这一问题的解决转向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即认为良好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与国家向善相关,而国家向善又与国家理性和对权力的制约分不开。不论启蒙抑或后启蒙思想家都是如此。这是近现代意义上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和管理思想诞生的标志。尽管思想家们大多同意德行和信仰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们更愿意相信,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没有国家理性和对权力的有效限制,国家向善和良好秩序的建立只能是一种愿望(洛克,1981;孟德斯鸠,1982)。因此,一方面,国家(政府)在保护所有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或法人团体)的强暴方面实乃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一旦政府为达到此目的而成功垄断了实施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有了威胁个人自由和滥用权力的可能(不论什么国家,近现代这方面的事例实在是很多),因此要维续国家善治首先需要对权力加以限制。这也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的伟大目标。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行政强力机构(官僚机构)自身难以很好地自我约束,因为不管这一机构由谁组成(哪怕是由“圣贤”组成)都会因自身的弱点(圣贤毕竟是人因而也有弱点)而存在自身利益或易受利益集团影响。其次主权的划分和代议制尽管能够起到相当的制约作用,但是单凭民主代议机构来保证善治仍缺乏坚实的可靠性。亚里士多德(1981:卷四1292a-11)很早就说过,在平民民主制中,城邦公民大会常以依公众决议所宣布的“命令”代替法律,在此,“民众成为一位集体君主”而趋于专制。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代议机构一旦被赋予无限权力的确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制定与正义背道而驰的法规”(Schweitzer,1923:1)而成为某种暴政的工具。因此,正如波普(1999)所言,以为只要采用民主方式对权力进行控制就能防止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既然权力制衡权力的做法并非完满和十分可靠的,那么就必须在国家以外找寻有效的制约力量。这个力量便是与国家既相对立又密切相关的公民社会。现代西方公民社会起源于中世纪盛期的城市公社或市镇自治体(commune)。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表明它们是城市“文明的结果”,而“非自然产物”(达仁道夫,2000:36)。韦伯(2005a)指出,它们一开始就是在同王权和贵族封建权力的抗争中崛起的。因此,自由对公民社会成员来说弥足珍贵。“不自由,毋宁死!”或费里斯兰(Frisian)民谚“宁死不当奴隶”,是他们(同时也是现代西方人)心灵建构的特性和真实写照。按照洛克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社会与国家分属不同的领域,社会由于是“形成的”,因而是丰富多彩和充满生机的,而国家因为是建构的,所以死气沉沉、单调乏味。也就是说,社会是自由和创造之所在,而国家是限制和卫护之所在。国家与社会分离是人们自由和保持创造力的基本保证。一方面,公民社会需要国家的保护、提供秩序和服务,没有国家,人们就会回到失序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有限私性主权(相对自治)和自主活动领域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因为“没有公民社会,民主和法治国家将顶不上多少作用”,“自由依旧是一根摇晃不定的风中芦苇”(达仁道夫,2000:36)。公民社会是法与自由的媒介物。因此,在西方人看来,重要的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允许很多不受政府干预、合法的(自生自灭的)社团的存在(它们也许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富有创造性)。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而其行为又没有对他者构成妨碍的,国家权力机构就不能任意干预。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有合法的自治性、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旦权力机构违法并侵害社会的利益,公民社会有权抗拒,并通过强大的社会力量和公共沟通领域合法地使之得到纠正,这也就是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制约以及使善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是在相互制约和互动中发展的(Held,1983;Pelczynski,1985)。 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自近代以来有一个明显变化的过程。当近代早期洛克等人说公民社会是自由之所在的时候,黑格尔(1979)当然不同意洛克等人的观点。因为黑格尔敏锐地观察到他那个时代公民社会分裂的状况,看到了公民社会的自由只是有产者的权利,对于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底层没有实质意义。因此,早期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实乃“绅士社会”。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明显无法将自由普及共享。于是,黑格尔不仅诉诸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更寄希望于一个中立和超然的国家。认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理性,能够超越公民社会自私的追求,即关心普遍而不是只顾特殊。① 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当然受到马克思(1956/1844)的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似乎是分开的,但决非中立、超脱。资产阶级表面上看控制着经济,但实质上是通过控制国家来实现控制经济的。黑格尔的国家将阶级分裂建制化,其不仅不能对社会采取普遍、公正的态度以克服异化,反而本身就是异化的产物。因此,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国家不会使“认可”和尊严具有普遍性。 不过,历史还是朝着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的。当代西方现实情形表明,不论洛克还是黑格尔的观点尽管似乎不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实际,但却接近当代的现实情况。如今,一方面,社会底层通过公民社会的一种形式——工会——获得了过去难以比拟的“社会权力”并以此抗拒资本和官僚权力可能的侵害,另一方面,随着中等阶层日益在社会中占多数,国家管理机构也逐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庸和超然(反映中等阶层意识)。当然,即便如此,韦伯有关人们谨防官僚机构成为最大利益集团或受某些压力集团影响的告诫,必须警钟长鸣。官僚机构能否公正运转除了内部治理、国家权力划分与制衡之外,还取决于公民社会对它的制约。在西方,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力量的存在,防止权力的滥用才得到有效保证,自由与秩序基本上保持均衡才有可能。这是当代西方社会稳定与和谐(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和谐)的基础。 不容置疑,西方国家在逐步转向国家理性和善治的同时,国家权力也在扩张。这突出表现在,原属于私人领域的经济、贸易、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逐渐作为公共问题而受到国家干预。国家不再扮演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守夜人”角色,而成为积极的干预者。这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分工精细化、组织化和复杂化的反映,同时也是不同于共同体的现代陌生人抽象社会难当此任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尽管古老的斯巴达幻象在西方仍不时闪现,但随着自由文化在现代的发展,以往那种“全景监狱式”监管在社会中已受到普遍唾弃。那么在国家权力不得不扩张的条件下应当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和管理呢?以下大概是现代西方社会在此问题上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其一,尊重法治(不同于法制)。远在西方文化的源头亚里士多德(1981:1287a-1287b30)就说过,民主社会的基础是“法治”,“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神祇在此当指“逻各斯”)。在现代西方,这已逐渐形成传统(尽管有反复),即社会建设和管理逐渐由过去的以行政为治转为“以法律为治”,前面所引李普曼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要求法别于甚至高于政治而“相对自治”,亦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伯尔曼,1993:44)。挪用英国古老名言来说,就是政府不在任何人之下,但必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因为法律创造了政府。当然,不仅国家行政权力要尊重法治,公民社会也要尊重法治,也就是说,权力与自由都要接受法律的“规训”,这也就是所谓“文明之规训”。没有法治就没有作为善治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法律的尽头是暴政的起点”这一洛克的格言道出了其本质。 其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要理性、适度,懂得常态与非常态管理之别并保护和爱护正当 ① 黑格尔心中的理想典型是被美化了的普鲁士君主立宪国家(Avineri,1972)。 的自发性。如奥地利著名经济和社会理论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言(Mises,1949:239),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作为社会的强力机构,“政府的目的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政府不仅“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而且“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遭其他人的侵犯”。米塞斯的这些话对于常态的公民社会和私领域人们的活动也应当适用。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政府通过法律只提供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抽象的普遍秩序和规则(哈耶克,2000:460),市场和公民社会在这种秩序下实行合法的自我管理或自治(自治是公民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只有这样,自发性和自组织活动才能合理有效展开,社会才能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只有当市场失灵以及公民社会失序的时候,政府才给予必要的干预。阿玛蒂亚•森言:“成功的资本主义的经验不仅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还建立在制度综合的发展基础上,而市场经济仅仅是其一部分。看不见的手经常高度依赖于看得见的手”(Sen,2010/2006)。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也要受到法治的限制,政府只有在自由、开放社会普遍规则和法治范围内才能合法地干预市场和社会。 其三,国家与公民社会尽可能地采取协商、合作的方式互动,也就是法治下的文明互动。这要求:一方面是政府的文明化(civilization of government),政府要从几个世纪以来习惯的“全景监狱式”监管模式转变到尊重法律的服务型模式上来,管理要富有理性和人性化;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也必须遵守一视同仁的普遍规则,使自身行为受到“规训”,成为“文明社会”、“礼貌社会”或“绅士社会”(文明、礼貌、宽容、无暴力、文质彬彬和富有绅士精神是公民社会的传统),并限制过激行为。当各个方面的相关者都被纳入法治化程序的时候,社会秩序受到的威胁被降到最低限度。 其四,在当代西方世界,“大社会”与“小政府”(“最小国家”)之论已不再为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提倡(哈耶克,2000:332),原因是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即使在西方,大社会也需要增加政府活动的范围。这是政府从统治类型向服务和管理类型转变的反映。哈耶克曾说过,在市场能够为人们提供有效服务的地方,诉诸市场当然是最佳方法,但是,在市场无法胜任的地方,就不能不依靠发挥政府的功能了。不过,为了防止人们担心的政府过于强大而发生侵害,一方面人们必须把政府的政治统治(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与服务性职能明确界分开来,另一方面不能把赋予前一种职能的权威和尊严同样赋予后一种职能。换言之,前者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而后者不具这种性质。因此,政府活动范围的增大主要大在服务职能上而非统治职能上。政府的服务性职能是一种合作、协商和与市场相联系的职能,而非高压强制职能。因此,在当今时代政府服务性职能扩大的同时,必须谨防政府对服务的垄断(哈耶克,2000:333,485)。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f0509d4cbd376eeaeaad1f34693daef5ef7130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