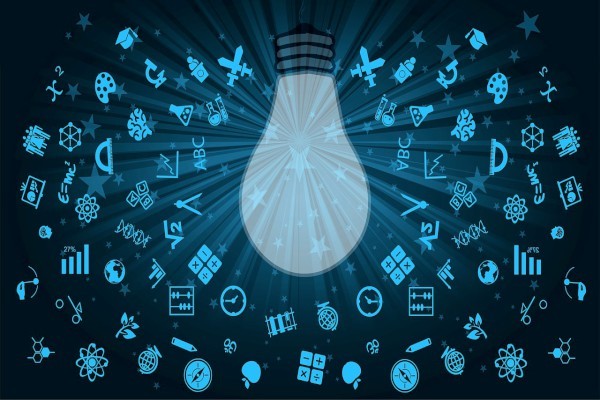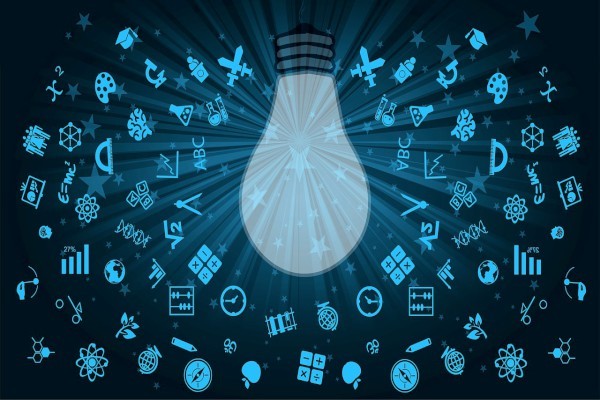【#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荷花淀”派的文学边缘性原因探究》,欢迎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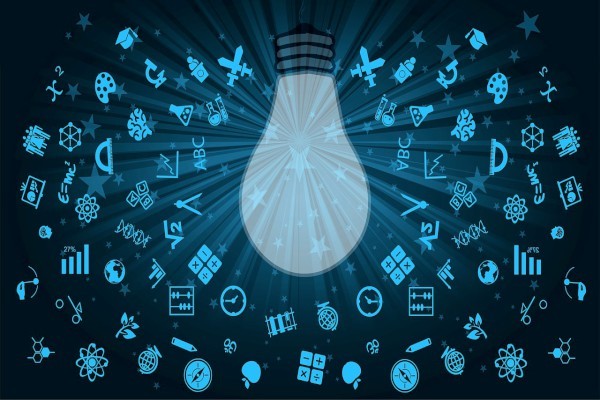
摘 要: 20世纪40年代,“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在解放区文学中并驾齐驱,“荷花淀派”清新的艺术特色为中国文学流派提供了明亮的色彩。但是,自创作以来它却始终处于文学的边缘位置。本文以“荷花淀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孙犁为关注的焦点,以时间为发展阶段,结合每个阶段的创作特色及“荷花淀派”成员的风格转向来探究其边缘化的原因,从中体会此文学流派的非凡价值。 关键词: 孙犁 文学边缘 时代主流 市场化 荷花淀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的重要一隅。它以孙犁为旗帜,以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受到孙犁培养和直接影响的作家为主要成员,以《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青枝绿叶》等为代表作。“荷花淀派”曾与“山药蛋派”并驾齐驱,轰动一时,也在后起作家的努力下发扬壮大。 然而,“荷花淀派”这一曾经有着影响的文学流派却始终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甚至是否存在“荷花淀派”,或者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是否具有存在的意义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少有名的中青年作家说过自己从孙犁那里懂得了文学,孙犁的许多作品是当代读者公认的现当代文学的瑰宝。学者的讨论显示出“荷花淀派”的边缘性,作家的继承和读者的吹捧证明着“荷花淀派”的成就。这不禁形成一个悖论:纯实力与被关注的不成正比。本文以“荷花淀派”的主将孙犁为关注点,在探究“荷花淀派”处于文学边缘的原因中深刻理解其“另类”中别样的价值及意义。 自1939年进入文坛到1945年,是孙犁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将冀中地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可歌可泣的斗争交织在白洋淀水乡如诗如画的背景上,诗情画意中洋溢着人民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丈夫》中的媳妇、《荷花淀》中的水生嫂等女性明大局、识大体,承受着比男人更多的困难和磨难,显示着时代的美。《荷花淀》、《嘱咐》等作品一发表,就几乎家喻户晓,带着浓郁的芳香立刻吹遍了解放区和大后方。 “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男女的勤劳明朗的性格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既有勇敢矫健的革命行为,但也有一些委婉细腻的男女爱情,有时这种细致的感触写得太生动,就和战斗气氛不太相称,因而也就多少损害了作品应有的成就。”[1]《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中肯地评价孙犁成就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作品与时代的不相适应性。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文学确立了为文艺兵服务的思想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歌颂新政权、新生活,表现人民激情地建设新社会,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手法是对作家们的基本要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表现着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书写着解放区的生活和生产斗争。然而,“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2]的文学观念下,孙犁将战争的残酷、人民如火如荼地建设解放区的情景淹没在华北泥土和北方水乡的清新气息里,“略去了战争厮杀的残酷,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多情女人与有情男人的眉目传情甚或打情骂俏的浪漫场景的描绘”[3]中,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婉约”之作就显得“另类”,作品“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成为了“革命文学的多余人”[4]。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孙犁随部队进城,分配到《天津日报》工作,由此进入孙犁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同年创作的《村歌》、《山地回忆》是其代表作。《村歌》描写性格矛盾的女青年双媚,喜赶集上庙和演戏,做事没个分寸,可就是她,又勇于承担责任,努力改造落后的互助组。“刻画了一个拥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5]。这也成为孙犁被主流批评界公认的“诟病”。《山地回忆》中作者用对战争年代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追忆来表达对城市冷漠人际关系的不满。孙犁一改创作初期的浪漫与乐观,格调转向严峻和低沉。1949年,全国一片欢腾,全国人民沉浸在“站起来”的欢腾里,孙犁的这一风格显然不受欢迎,即便到现在评论界对孙犁这一时期的作品评论也十分欠缺。1956年孙犁进入创作的第三阶段。孙犁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讲述的是七七事变后,冀中平原子午镇和五龙堂村庄的变迁史。作者将双重身份集中于一身,主人公知识女性李佩钟既是抗日政府的县长,肩负着解放民众的历史重任;又是大财主的儿媳,反动区长的妻子,是革命的对象。然而,一直致力于中短篇创作的孙犁,在这部小说中显示出在驾驭长篇体制上功力的欠缺。《铁木前传》以乡村中的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的友情和友情的破裂,表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小满儿这个有争议的边缘女性成为作者窥探人性和哲学思考的化身。相比过去,孙犁的笔法成熟了许多,显示出深沉和凝重的风格,得到了读者的肯定,为自己的创作赢得了新天地。但是贯穿在作品中的情绪和气质,仍是孙犁一贯的风格:散文化的行文结构中贯穿人生的悲喜剧,对女性的欣赏及感情的投入,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生活画卷中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强调“典型环境及典型人物的塑造”,提倡“正面描写时代的巨大斗争生活”。“颂歌”时代下,浩然的《金光大道》、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小说,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政治抒情诗显然更适合时代的发展,孙犁“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与那些紧跟时代的高音者实在无法和谐共奏。“对我们时代的风貌进行更广泛的描绘,对人物性格进行更完整、更深刻的刻画”[6],是文学批评家对孙犁的期待,更是时代对孙犁的期待。 1956年春,孙犁突发了一种神经衰弱症,由此终止小说创作近20年。这期间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在《戏的梦》中他说道:“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袅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伤太重了,它要休生养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粉碎“四人帮”后,孙犁“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7],由此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四个阶段,也是他人生自40年代后第二个创作高峰,创作了《晚华集》、《秀露集》、《云斋小说》等多个散文集、回忆录及小说作品。“文革”时期,孙犁见证了政治骗子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欺骗;目睹了昔日的战友、同志身遭祸殃;自己又蹲过“牛棚”,经历丧妻的悲苦,忍受病症的折磨。读着写作时间持续了10来年的《芸斋小说》时,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位经历着人生的悲悲喜喜,目睹了“文革”中是是非非的老人对人生苍老的了悟。这位历尽沧桑的寂寞老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对往事的絮絮自语中表达着真实而独立的反思和思考。对不喜欢的,他嫉恶如仇:《心脏病》中坦言“文革”中的无数事实,让他“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并对其“采取了极其蔑视的态度”;《宴会》写自己曾经亲眼目睹了战友由于托派问题的牵连而失踪;《王婉》客观地描述了现实被逼下的人性腐蚀;《新年杂忆》里对文学评论家专制化、权威化等文坛上不良现象进行了鞭挞和讨伐。对自己喜欢的,他爱美若狂:《春天的风》、《我留下了声音》等在对善和美的褒扬中展现出孙犁依旧不变的青春热情;《亡人逸事》、《幻觉》等作品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进行反思,在对青春年华的无限眷恋,纯真爱情的怀念、珍惜与赞美中独自咀嚼着孤独老人的寂寞与苦涩。《无花果》写自己正值壮年而又身患重病时与一位农村姑娘那未能开花结果的恋情。《石榴》、《忆梅读〈易〉》、《我留下了声音》等作品中,孙犁坦陈了埋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爱情记忆,年轻时对学生梅、山东青岛疗养院某护理员、文学社团的姑娘的爱慕,在情感的反思中体现出作家晚年对年轻时不曾热烈爱过的微憾;对他人爱恋却没有因此而移情别恋更衬托出孙犁坚定的人生操守。为了照顾他的名声,塑造一个完美的孙犁形象,编辑好心地删去这类文字,孙犁却依旧坚持,“我一生中,做过很多错事,鲁莽事,荒唐事。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删不胜删”[8]。孙犁晚年的写作抛弃了一切世俗的欲念,傲岸和倔强地将自己的情感隐私公开放在书面上,打破了道德完美的丈夫形象、作家形象,给多年信任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孙犁。80年代年代前期,孙犁曾明确声称要“歌颂当今施政,诅咒十年动乱”,可以说是迎合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新时期潮流,是很“入流”的。但是,年轻时就自觉地避开慷慨激昂的时代“主旋律”的孙犁,晚年就更没有“入流”的愿望和可能了的。“余信天命,屈服客观,顺应自然”[9],他不关心读者反应、自己名声、作品销量,而这些正是八、九十年代主流作家们关心的事,也是读者、评论媒介证明作家地位、身份的象征。他拒绝刘绍棠来邀请他扛“乡土文学”大旗,坚决反对“荷花淀派”的提法:他与市场化的时代又一次的格格不入。在垂暮之年,他坚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走向孤独与沉默,边缘写作,边缘生存,直到生命的终点。 早年的孙犁游离于主流政治的“网”,风格转向期间因作品不成熟而淡出评论者的视野;晚年的孙犁远离市场化的“网”,因此其作品一直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就不足为怪了。受到孙犁的关怀、培养,并直接受其影响,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在创作中坚持并创新,促进了“荷花淀派”的发扬光大。刘绍棠始终把孙犁的作品奉为自己效法的楷模,在他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清纯的女性形象,一丈青大娘、碧桃、青凤、柳叶眉、蓑嫂、春柳嫂子、蛾眉等,散发着清新、俊逸的风格。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浆声》,韩映山的《紫苇集》等小说,“孙犁味”扑面而来。然而,学习孙犁的风格只是他们的基础和起跳板,随着创作的成熟,“孙犁味”便渐渐淡了。从维熙自创了“大墙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等作品题材突破只写农村,创作方法不再仅限于白描、对话,风格也从荷花淀派最初的清新转向深沉。《春草》、《蒲柳人家》等作品中,刘绍棠已变得俊秀挺拔,深思沉着。五十年代中后期,韩映山曾经写过一些标准的“荷花淀”作品,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读到他的新作。“荷花淀派”后起作家中一些风格发生转向,新作不多,由此导致“荷花淀派”在文学圈中影响力不大,是造成“荷花淀派”处在边缘位置的又一原因。 “荷花淀派”的边缘主要来自于以孙犁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风格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背离。初期的“荷花淀派”为自己编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网,它清新淡雅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凝重深沉。它惨淡经营、恪守原则,在茫茫沧海里,成为了不显眼的一粟。但是,它远离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回避和躲闪着时代、政治赋予文学的常规模式,摈弃意识形态主导的程式化、艺术手法的规范化运作,在题材的新颖、风格的清新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历史话语掩盖的历史,创造了“‘民间隐形结构’的典范文本”[1]。即使处在文学的边缘,也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这张独特的网让中国的文学流派多了明亮的的一隅,即使在黑暗的年代,也给人以信心和希望。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9eb1784d1d233d4b14e852458fb770bf78a3bd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