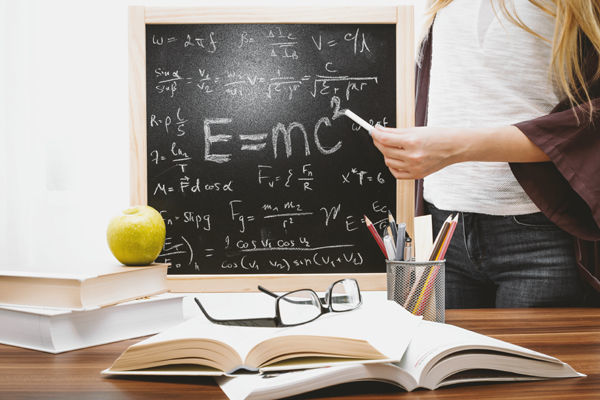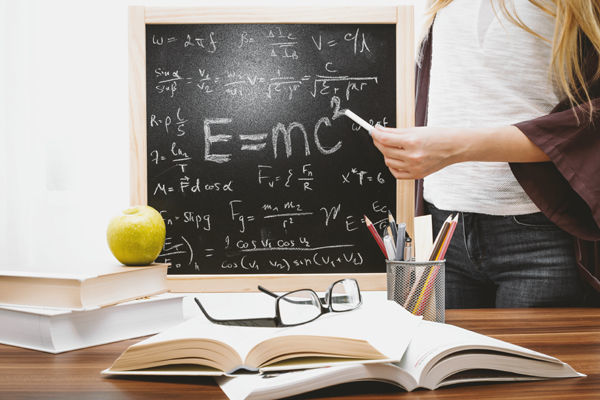【#第一文档网# 导语】以下是®第一文档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白蛇传说的女性主义研究》,欢迎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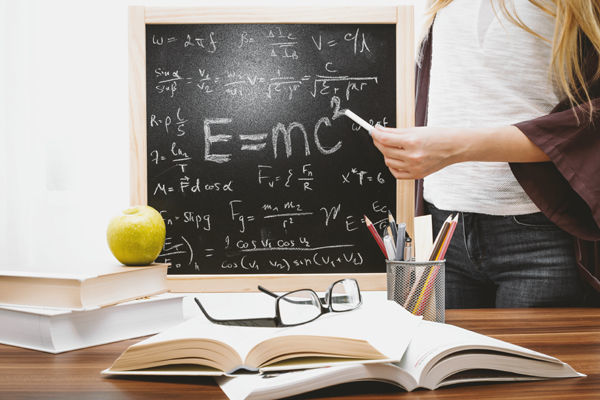
白蛇传说的女性主义研究 黄宝富 左继华 女性屈从于男性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观念,导致女性主体在社会权威话语序列中缺乏塑造自我意象的文化力量,女性形象在男权话语之下被编造或被分裂。符合男性欲望和想象的女性意象,被描绘为温顺可爱的天使;而违逆男性规训的女性形象,则被无限制地妖魔化。蛇的意象,因为柔软绵长的外貌和伏地而行的姿态,成为男性话语描绘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的想象符号,又源于蛇的神秘质地和毒性攻击性被赋予和生成了女性性格的阴险、狡猾、毒辣等负面定义。白蛇的女性传说,在历史叙述中不断变异和变化,然而,总是难以摆脱被男性描述的依附型命运。 “任何‘历史’不过都是一种文本的修辞活动,是一种‘修辞想象’,因为在‘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的本文’之间,永远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对应关系,更不可能是对等关系。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实际都是作为文本的历史,而‘文本’不但取决于客观的历史,更是取决于写作者的修辞态度,取决于他的解释方式、解释角度与价值立场。”① 女性的白蛇传说,就是男性世界的一种修辞想象,白蛇的性格与行为,随着男权意识的思想变动而发生叙事变化。 一、蛇意象:男性想象编写的女性隐喻 蛇形象与女性陈述的文学联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郭璞注《山海经·大荒西经》,“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在男性控制的原始思维之中,中华民族的始祖女神为善变的人蛇结合之体,这无疑为后世的白蛇传说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联想资源。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像设想他们自己一样设想一切存在物,并把他们熟知和真切意识到的那些品质移植到每一个对象上”,“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对原因无知的状态之中,而同时他们又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感到非常焦虑,于是乎,他们直接承认自己对拥有情感和理智的不可见力量的依赖,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些不断引发他们去思考的未知的原因,由于总是以同一种模样出现,也就被理解为属于同一类型了。为了让他们与我们自己更近似,我们把理性和激情、有时甚至是人的四肢外形赋予他们。”②人类将自我生命所具有的“灵性”赋予万事万物的宗教意识和神话思维,使渊源深远的白蛇传说,承载着男权想象对于女性的形象描绘、道德评判和时代阐释,然后以“一种模式”不断在文学、戏曲、影视中重复出现。 唐鬼谷子志怪小说《李黄》,可以视为白蛇传说的发源滥觞。故事原发地为“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唐都长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极尽美艳,“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素裙粲然,凝质姣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然而,美女毒蛇,李黄与白衣女子度过三天快乐无比的日子,回家后,“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最后发现与李黄交往的只是幻化女体的“巨白蛇”而已,这无疑是男性对于女性妖魔化的想象描述和心理恐惧。明洪楩的《清平山堂话本》卷一,收录据说编纂于南宋的话本《西湖三塔记》,故事发生地转移至宋都临安,话本中的白衣女子,“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美丽的女性角色形象却与其毒辣的蛇蝎心肠和凶狠的淫荡行为形成巨大的道德落差,当“白娘娘”掳掠到年轻貌美的男性“新人”,即将面黄肌瘦的“旧人”开膛破肚、以其心肝下酒。两部作品中的“美女蛇”的外貌都异常娇艳,只是李黄是主动接近“白蛇”,而李黄死后,白蛇也未受任何惩罚;而《西湖三塔记》中的男性奚宣赞为被动受掳,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白蛇”也被永生囚禁。男性话语对于女性的形貌描写或者说审美认同没有变化,对于女 性的“妖怪”本质与“祸害”指向,被延伸和确定。 明天启年间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故事人物和情节事件相对定型的“白蛇传”话本。《李黄》的叙述篇幅为900字左右,《西湖三塔记》的故事篇幅为4900字左右,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叙事长度为18000字左右,女性形象的赞美性描写依旧,白娘子被描绘为:樱桃口、榴子牙、娇滴滴声音、秋波频转,满面春风、如花似玉的美妇人,然而其人形蛇体“吊桶来大的蟒蛇”的“妖怪”性质并没有被时代发展所解构,而且凶残的本性并无变化,“我如今实对你说,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虽然话本之中并无白娘子残害生灵的事件细节,可是对女性的蛇性想象维持原初的男性界定。冯梦龙版本的白蛇传说,似乎描述了女性主动追求幸福的善良愿望和渴求自由的坚强性格,“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一见便蒙错爱。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与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对,却不是好?”可是,文本结尾的“警世通言”,“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却明显地昭示了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道德差异,“世人”为主流的男性权威世界,而女性角色却负有“色”、“邪”、“恶”的否定性判断。 清乾隆三年,黄图珌编撰的《雷峰塔传奇》,是白蛇传说从话本小说向戏曲文本转移的如今尚存的最早剧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方成培创作的集大成的传奇剧本《雷峰塔传奇》问世,方版剧作在民间梨园久演不衰、脍炙人口,他将白娘子的“蛇妖”身份智慧地置换为“蛇仙”,并且增加白娘子怀孕生子的人性化情节,白娘子的“兽性格”被人化为中国妇女的典型品质,然而,其“蛇躯体”的异化本质并未动摇,人们已经可怕地习惯于白娘子或者说女性蛇意象的隐喻惯例。1955年5月,田汉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创作,终于定稿出版《白蛇传》,他将许宣更名为许仙,大胆删减传统剧作曲目,仅留“游湖”、“结亲”、“查白”、“说许”、“酒变”、“守山”、“盗草”、“释疑”、“上山”、“渡江”、“索夫”、“水斗”、“逃山”、“断桥”、“合钵”、“倒塔”16场戏。田汉版白蛇传说在新中国舞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思想的认同,它几乎将白娘子塑造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反封建神话,白娘子的蛇妖气息被清理、被清除,“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劝雄黄。你忍心将我诳,才对双星盟誓愿,你又随法海入禅堂。你忍心叫我断肠,平日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还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败亡,可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云愁雾惨、波翻浪滚、战鼓连天响,你袖手旁观在山岗。手摸胸膛你想一想,你有何面目来见妻房?”,断桥相会中白素贞黯然神伤的唱词,把一个独立抵抗世界的女子的百转柔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对许仙们的批判中体现出革命时期的男性想象,然而,白娘子,终究还只是具有反抗意识的蛇意象。 二、塔象征:女性必须规训的道德暗示 在白蛇传说的历史序列里,可以比较清晰地领会到男权世界的话语霸权对于女性形象、女性品质和女性命运的权威编排,女性美艳的肉身,是一种隐藏着“蛇意识”的致命诱惑,女性如白蛇般的本能欲望,会蛊惑李黄、奚宣赞、许宣、许仙们摇摆的自我意识,所以,奚真人、法海和尚会很尽职地唤醒他们的男性意识,然后合力以象征性的“塔”将女性的自由和欲望镇压和囚禁。李黄,以其男性躯体的恐怖牺牲,换取对于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名实不符、外美内恶的中伤和攻讦,而且逃脱惩罚消失影踪的白蛇,使女性具有奸诈狡猾的历史暗喻。奚宣赞,则完全是一个见证白娘娘充满淫荡的性欲望和残害男性身心的受害者,因此,寄居于蛇体的女性肉体的生命权必须被禁锢,代表男权话语力量的奚真人,轻易地收服白蛇以“白塔”镇其于西湖之内,在公众视野之中规训了女性的公然反抗,然后,世界一切太平,奚宣赞得以“百年而终”,文末还附诗赞曰:“只因湖内生三怪,至使真人到此间。今日捉来 藏箧内,万年千载得平安。”塔的男性隐喻,塔意象的权力仪式和政治意义,开始在白蛇传说中彰显其重要的“规训、控制、惩罚”的象征意味。 在冯梦龙的男性想象里,不受“规训”的“寡居”的白娘子,竟然随心率性地突破女性的耻辱感和男性赋予的必须具有的女性操守,主动积极、百折不饶地追寻自我的幸福快乐,这种突围传统男权意识形态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行为,强烈地动摇了男性把持的社会秩序和男性主持的社会道德,这是令男性恐惧的觉醒力量。当许宣见了白娘子之后,“当夜思量那妇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情意相浓。不想金鸡叫一声,却是南柯一梦。正是: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对于女性的情欲幻想和对于女性的“红颜祸害”的矛盾情结,在女性“蛇”本性的描绘中瞬息间毫无悬念地倾向男权阵营,“白娘子放出迷人声态,颠鸾倒凤,百媚千娇,喜得许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见之晚”,夫妻之情难敌男权意识,当作为男权世界控制力代表的法海禅师,打击、掌控了违背男性限定的白娘子,将白娘子置于钵盂内,然后“将钵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砖运石,砌成一塔。后来许宣化缘,砌成了七层宝塔。千年万载,白蛇和青鱼不能出世”,许宣立马成为坚定和坚强的男权卫士,化缘砌七层塔,永世囚禁白蛇的身躯和自由,这是精心设计的征服和限制女性自觉意识的公共景观,“这种持续的男性主宰是男性对女性施暴的结果。社会结构本身说明了一种历史性持续的体力上的威胁”③,许仙与法海,是“施暴”女性的男性话语的社会合谋者,只不过两者在男权世界区分于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地位而已。 从话本中匍匐于地的“蛇妖”到戏曲中修行千年的“蛇仙”,白娘子似乎完成了“人性化”的角色转变,她美丽和善良并重、温柔和持家互倚、痴恋与坚韧相谐,白娘子从而“被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理想的妻子和悲悯的母亲,白娘子身上原本具有的“美丽”与“恐惧”的双重气质,尤其是“非人”的“兽性”的女性欲望,被男权世界“合法化”的伦理纲常所遮蔽和覆盖,而且,白娘子在戏曲剧目中的“被生育”事件,使她蛇性的体内真正植入了人的元素。崇高的母亲身份,抹平了白娘子的异类分界,将白蛇的身体形式整合为话语权力认可的规范主体和理想性格,从而使男性的权力意志掩盖和抑制了女性个体的个别性意识。被“驯化”、被“驯服”的白娘子,因为其自身的非族类的差别身份,还是被无情冷酷的男权力量压迫和禁锢在雷峰塔之下,可见,女性作为男权话语控制的服从者和屈从者,无法超越和超脱其从属者的女性境遇。戏曲版白蛇传说,为迎合受众的团圆情结,添加了“祭塔”、“捷婚”、“佛圆”等雷峰塔垮塌、母子相聚的光明细节,反而解构了白蛇传说的悲剧力量,而压制在女性身份上的无形之塔依然耸立。 ①王侃.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31 ② (英) 大卫·休谟.宗教的自然史[M].徐晓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19 ③(美)迈克尔·莱恩.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M].赵炎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5 (作者单位:黄宝富,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左继华,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9dd7c363968011ca30091f5.html